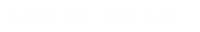вҖңж—әд»”е°Ҹд№”вҖқпјҢиў«иө·иҜү( дәҢ )
жі•йҷўе®ЎзҗҶи®Өдёә пјҢ з”ІжҹҗеңЁжҹҗе№іеҸ°е……еҖјеҗҺеҗ‘д№ҷжҹҗжүҖеңЁзӣҙж’ӯй—ҙжү“иөҸзӨјзү© пјҢ зі»е…¶иҮӘж„ҝеӨ„еҲҶиҙўдә§зҡ„иЎҢдёә пјҢ иҜҘиө дёҺиЎҢдёәе·Із»Ҹе®ҢжҲҗ гҖӮ з”ІжҹҗжңӘиғҪдёҫиҜҒиҜҒжҳҺеӯҳеңЁжі•е®ҡзҡ„иө дёҺеҸҜж’Өй”Җжғ…еҪў пјҢ й©іеӣһе…¶иҰҒжұӮйҖҖж¬ҫзҡ„иҜ·жұӮ гҖӮ
дёҖдәӣжғ…еҶөдёӢ пјҢ йғЁеҲҶжү“иөҸж¬ҫиў«и®Өе®ҡдёәиө дёҺ гҖӮ д»Ҡе№ҙ6жңҲ пјҢ зҰҸе»әзңҒйҫҷеІ©еёӮдёӯзә§дәәж°‘жі•йҷўжҠ«йңІ пјҢ жҹҗе№іеҸ°з”ЁжҲ·з”·еӯҗйҖҡиҝҮиҜҘе№іеҸ°еңЁеҚҠе№ҙеҶ…еҗ‘еҘідё»ж’ӯжү“иөҸдәҶд»·еҖј148дёҮдҪҷе…ғ пјҢ еҗҺз§°еҘідё»ж’ӯзҡ„иЎҢдёәеұһеј•иҜұжү“иөҸиҰҒжұӮиҝ”иҝҳ гҖӮ
жі•йҷўе®ЎзҗҶи®Өдёә пјҢ дёҖиҲ¬иҖҢиЁҖ пјҢ з”ЁжҲ·еңЁзӣҙж’ӯе№іеҸ°дёҠеҹәдәҺдё»ж’ӯзҡ„иЎЁжј”иҙЁйҮҸиҝӣиЎҢжү“иөҸ пјҢ еұһдәҺиҺ·еҫ—зІҫзҘһж–ҮеҢ–жңҚеҠЎеҗҺзҡ„жӯЈеёёж¶Ҳиҙ№иЎҢдёә пјҢ жһ„жҲҗзҪ‘з»ңжңҚеҠЎеҗҲеҗҢ гҖӮ дҪҶжң¬жЎҲдёӯ пјҢ дёӨдәәзҡ„дә’еҠЁе·Іи¶…еҮәжҷ®йҖҡдё»ж’ӯдёҺзІүдёқе…ізі» пјҢ еҘідё»ж’ӯжҳҺзҹҘиҜҘз”·еӯҗе·Іе©ҡ пјҢ д»Қд»ҘжҒӢдәәеҗҚд№үдәӨеҫҖ пјҢ 并д»Ҙз»“е©ҡдёәиҜұеј•дҝғдҪҝе…¶й«ҳйўқжү“иөҸ гҖӮ йүҙдәҺжү“иөҸйҮ‘йўқиҝңи¶…дёҖиҲ¬еЁұд№җж¶Ҳиҙ№ж°ҙе№і пјҢ еә”и®Өе®ҡйғЁеҲҶжү“иөҸзі»дёәз»ҙзі»е©ҡеӨ–дёҚжӯЈеҪ“е…ізі»зҡ„иө дёҺиЎҢдёә пјҢ дәҢдәәе®һиҙЁдёҠеҪўжҲҗдҫқжүҳе№іеҸ°зҡ„иө дёҺеҗҲеҗҢе…ізі» гҖӮ
еј е…Ҳж—әи§ЈйҮҠ пјҢ дёҖж—Ұиў«и®Өе®ҡдёәиө дёҺ пјҢ йҷӨйқһжҳҜйҷ„жқЎд»¶зҡ„иө дёҺжңӘжҲҗ пјҢ еҗҰеҲҷжү“иөҸиЎҢдёәе·Із”ҹж•Ҳ пјҢ иҝ”иҝҳеҮ д№Һж— жңӣ гҖӮ иҝҷдёҖжјҸжҙһжҲ–дҪҝеҫ—дёҖдәӣдё»ж’ӯдё“й—Ёз ”з©¶вҖңиҜқжңҜвҖқе’ҢвҖңеңәжҷҜвҖқ пјҢ иҜұеҜјзІүдёқжҠ•е…ҘйҮ‘й’ұе’Ңжғ…ж„ҹ гҖӮ вҖңдёҚе°‘жү“иөҸиҖ…еӣ жӯӨйҷ·е…Ҙз»ҸжөҺеӣ°еўғз”ҡиҮіеҝғзҗҶеҙ©жәғ пјҢ еёҢжңӣйҖҡиҝҮжӯӨжЎҲиғҪеј•иө·зӨҫдјҡиӯҰйҶ’ пјҢ жҺЁеҠЁжі•еҫӢе®Ңе–„гҖҒ规иҢғиЎҢдёҡд№ұиұЎ гҖӮ вҖқ
жңүзҡ„жү“иөҸжЎҲ件еҲҷиў«и®Өе®ҡдёәжңҚеҠЎеҗҲеҗҢ гҖӮ йҷ•иҘҝзңҒиҘҝе®үеёӮдёӯзә§дәәж°‘жі•йҷўжӣҫжҠ«йңІ пјҢ зәҰдёҖе№ҙж—¶й—ҙеҶ… пјҢ е·Іе©ҡз”·еӯҗиҙәжҹҗеңЁжҹҗзҪ‘з»ңзӣҙж’ӯе№іеҸ°жіЁеҶҢдәҶ3дёӘиҙҰеҸ· пјҢ и§ӮзңӢдё»ж’ӯеҫҗжҹҗзӣҙж’ӯ并жү“иөҸ13318ж¬Ў пјҢ жү“иөҸйҮ‘йўқи¶…25дёҮе…ғ гҖӮ 2019е№ҙ3жңҲ пјҢ дёӨдәәзәҝдёӢи§Ғйқў пјҢ 并д»Ҙжғ…дәәе…ізі»зӣёеӨ„иҮі2020е№ҙ3жңҲ пјҢ иҮідәҢдәәе…ізі»з»Ҳжӯў пјҢ иҙәжҹҗйҖҡиҝҮзҪ‘з»ңжү“иөҸе’ҢзәҝдёӢдәӨеҫҖе…ұдёәеҫҗжҹҗиҠұиҙ№32дёҮе…ғ гҖӮ
е…¶еҗҺ пјҢ иҙәжҹҗд№ӢеҰ»еҗ‘жі•йҷўжҸҗиө·иҜүи®ј пјҢ и®ӨдёәиҙәжҹҗжңӘз»Ҹе…¶е…Ғи®ё пјҢ е°ҶеӨ«еҰ»е…ұеҗҢиҙўдә§иө дёҺеҫҗжҹҗзҡ„иө дёҺеҗҲеҗҢж— ж•Ҳ пјҢ иҰҒжұӮеҫҗжҹҗе°Ҷзӣёе…іиҠұиҙ№жӮүж•°йҖҖеӣһ гҖӮ
иҘҝе®үдёӯйҷўе®ЎзҗҶеҗҺи®Өдёә пјҢ еҫҗжҹҗдёҺиҙәжҹҗд№Ӣй—ҙжҸҗдҫӣзӣҙж’ӯдёҺжү“иөҸзҡ„е…ізі»еұһдәҺеҗҲеҗҢе…ізі» гҖӮ иҜҘеҗҲеҗҢе…ізі»зү№ж®Ҡд№ӢеӨ„еңЁдәҺеҜ№еҫҗжҹҗзӣҙж’ӯиЎЁжј”зҡ„д»·еҖјзҡ„и®Өе®ҡ并йқһз”ұеҫҗжҹҗеҶіе®ҡ пјҢ иҖҢжҳҜз”ұиҙәжҹҗеҚ•ж–№еҶіе®ҡ гҖӮ дҪҶиҜҘжғ…еҶөдёҚиҝқеҸҚжі•еҫӢгҖҒиЎҢж”ҝ法规зҡ„ејәеҲ¶жҖ§и§„е®ҡ пјҢ дёҚеҪұе“ҚеҗҲеҗҢж•ҲеҠӣ гҖӮ
вҖңжі•е®ҳеңЁеҲӨж–ӯжҳҜеҗҰеә”йҖҖиҝҳжү“иөҸж¬ҫж—¶ пјҢ еҫҖеҫҖйңҖиҰҒз»“еҗҲе…·дҪ“жғ…еўғ пјҢ е®ЎжҹҘеҜ№д»·жҳҜеҗҰе……еҲҶгҖҒиЎҢдёәжҳҜеҗҰеҗҲд№Һе…¬еәҸиүҜдҝ—зӯүеӣ зҙ гҖӮ вҖқи–ӣеҶӣиЎЁзӨә пјҢ еңЁеҸёжі•е®һи·өдёӯ пјҢ жЎҲ件主иҰҒйӣҶдёӯдәҺиҜұеҜјдёҚеҪ“жү“иөҸе’ҢвҖңиҝҮеәҰжү“иөҸвҖқдёӨзұ»жғ…еҪў гҖӮ еүҚиҖ…еӨҡи§ҒдәҺйғЁеҲҶдё»ж’ӯйҖҡиҝҮжҡ—зӨәжҒӢзҲұе…ізі»гҖҒиҷҡжһ„иә«д»Ҫ пјҢ иҜұеҜји§Ӯдј—й«ҳйўқжү“иөҸ пјҢ иҖҢе®һйҷ…жғ…еҶөдёҺеЈ°з§°дёҚз¬Ұ пјҢ жі•йҷўеҸҜиғҪи®Өе®ҡеӯҳеңЁиҜҜеҜјжҲ–ж¬әиҜҲжҲҗеҲҶ пјҢ д»ҺиҖҢж”ҜжҢҒиҝ”иҝҳиҜ·жұӮ гҖӮ
еј е…Ҳж—әиЎҘе……жҢҮеҮә пјҢ еҪ“еӯҳеңЁиҜұйӘ—гҖҒж¬әиҜҲгҖҒиғҒиҝ«зӯүжғ…еҪўж—¶ пјҢ жҲҗе№ҙдәәжү“иөҸеҗҺиғҪиҰҒжұӮиҝ”иҝҳ гҖӮ д»–иҜҙ пјҢ д»Ҙжң¬жЎҲдёәдҫӢ пјҢ вҖңж—әд»”е°Ҹд№”вҖқжӣҫиҜұеҜјеҪ“дәӢдәәзҒҜзүҢеҲ·еҲ°20зә§еҸҜд»Ҙж·»еҠ з§Ғдәәеҫ®дҝЎзӯү гҖӮ иҝҳжңүдё»ж’ӯд»ҘжҒӢзҲұдёәеҗҚ пјҢ иҜұйӘ—зІүдёқжҲ–жү“иөҸдәәеҲ°е…¶жүҖеңЁеҹҺеёӮи§ҒйқўжҲ–еҸ‘з”ҹе…ізі» пјҢ з”ҡиҮіеҗ‘еӨҡж•°дәәйғҪеҸ‘еҮәзұ»дјјйӮҖзәҰдё”жІЎжңүе…‘зҺ° пјҢ еҲҷжһ„жҲҗиҜҲйӘ—жҲ–ж¬әиҜҲ гҖӮ иғҒиҝ«еҲҷжҳҜжҢҮдё»ж’ӯжҺҢжҸЎжү“иөҸдәәзҡ„йҡҗз§ҒжҲ–з§ҳеҜҶеҗҺ пјҢ д»Ҙжү“иөҸзҡ„еҪўејҸеҗ‘еҜ№ж–№зҙўиҰҒй’ұиҙў пјҢ вҖңе®һеҲҷжҳҜйҖҡиҝҮжү“иөҸзҡ„еҗҲжі•еӨ–иЎЈиҝӣиЎҢиғҒиҝ«вҖқ гҖӮ
ж¶үеҸҠеӨ«еҰ»е…ұеҗҢиҙўдә§зҡ„жү“иөҸд№ҹжҳҜдёҖз§Қеёёи§Ғзә зә· гҖӮ еј е…Ҳж—әжҢҮеҮә пјҢ еӨ«еҰ»дёҖж–№жңӘз»ҸеҜ№ж–№еҗҢж„Ҹ пјҢ ж“…иҮӘд»Ҙе…ұеҗҢиҙўдә§жү“иөҸ пјҢ еҸҰдёҖж–№еҸҜиЎҢдҪҝж’Өй”Җжқғ гҖӮ
еңЁвҖңиҝҮеәҰжү“иөҸвҖқдёӯ пјҢ жңүж—¶еҖҷиҝҳдјҡзүөеҮәжү“иөҸдәәдҪҝз”Ёе…¬ж¬ҫжҲ–йқһдёӘдәәй’ұиҙўй«ҳйўқжү“иөҸзҡ„жғ…еҶө гҖӮ и–ӣеҶӣиЎЁзӨә пјҢ жӣҫжңүеҚ•дҪҚеңЁиҝҪиөғж—¶ пјҢ зүөеҮәдјҡи®ЎжҢӘз”Ёе…¬ж¬ҫжү“иөҸзҡ„жЎҲдҫӢ гҖӮ жі•йҷўеңЁеӨ„зҗҶжӯӨзұ»жЎҲ件时 пјҢ дјҡз»“еҗҲйҮ‘йўқжҳҜеҗҰејӮеёёе·ЁеӨ§гҖҒдё»ж’ӯжҲ–е№іеҸ°жңүж— дёҚеҪ“иҜұеҜјгҖҒжү“иөҸзҡ„йў‘ж¬ЎгҖҒжү“иөҸж¬ҫзҡ„жқҘжәҗжҳҜеҗҰеҗҲжі•зӯүеӣ зҙ пјҢ еҶҚеҶіе®ҡжҳҜеҗҰиҝ”иҝҳеҸҠиҝ”иҝҳжҜ”дҫӢ гҖӮ
ж— и®әжҳҜдҪ•з§Қе®ҡжҖ§ пјҢ дёҫиҜҒйҡҫжҳҜиҫғдёәжҷ®йҒҚеӣ°еўғ гҖӮ и–ӣеҶӣжҢҮеҮә пјҢ зӣҙж’ӯжү“иөҸеӨҡе…·жңүеҚіж—¶жҖ§ пјҢ иҜҒжҚ®дҝқеӯҳеӣ°йҡҫ пјҢ зәҝдёҠзәҝдёӢдә’еҠЁзҡ„дәӨз»Үд№ҹдҪҝдәӢе®һи®Өе®ҡжӣҙеҠ еӨҚжқӮ гҖӮ
йҷӨдё»ж’ӯеӨ– пјҢ зӣҙж’ӯе№іеҸ°дәҰеёёиў«еҲ—дёәиў«е‘Ҡ гҖӮ еҢ—дә¬дә’иҒ”зҪ‘жі•йҷўжӣҫе®ЎзҗҶдёҖиө·з”ЁжҲ·иө·иҜүе№іеҸ°зҡ„жЎҲ件 гҖӮ иҜҘз”ЁжҲ·з§°дё»ж’ӯеӯҳеңЁвҖңиҜұеҜјжү“иөҸвҖқиЎҢдёә пјҢ е№іеҸ°зӣ‘з®ЎдёҚеҠӣ пјҢ иҜ·жұӮиҝ”иҝҳе…ЁйғЁжү“иөҸж¬ҫдёӨдёҮе…ғ гҖӮ жі•йҷўи®Өдёәз”ЁжҲ·иҮӘдё»жү“иөҸгҖҒж„ҸжҖқиЎЁзӨәзңҹе®һ пјҢ жңӘжһ„жҲҗж— ж•ҲжҲ–еҸҜж’Өй”ҖеҗҲеҗҢ пјҢ й©іеӣһе…¶е…ЁйғЁиҜүжұӮ гҖӮ
е…ідәҺжҳҜеҗҰдјҡиҝҪ究平еҸ°иҙЈд»» пјҢ еј е…Ҳж—әжҢҮеҮә пјҢ зӣ®еүҚе№іеҸ°зӣ‘з®ЎиҙЈд»»еӨ§йғЁеҲҶеұһдәҺеҲқжӯҘеҪўејҸеұӮйқўе®ЎжҹҘ пјҢ иҖҢйқһе®һиҙЁе®ЎжҹҘ гҖӮ д»–еқҰиЁҖ пјҢ еңЁзҺ°иЎҢжі•еҫӢжЎҶжһ¶дёӢ пјҢ е№іеҸ°иҙЈд»»зҡ„дёҫиҜҒеӯҳеңЁеӣ°йҡҫ гҖӮ вҖңжҲ‘们жЈҖзҙўиҝҮеӨ§йҮҸжЎҲдҫӢ пјҢ йҷӨйқһиғҪиҜҒжҳҺе…¶жҳҺзҹҘдё»ж’ӯеӯҳеңЁж¬әиҜҲд»Қж”ҫд»»дёҚз®Ў пјҢ еҗҰеҲҷиғңиҜүзҺҮжһҒдҪҺ гҖӮ вҖқ
жҺЁиҚҗйҳ…иҜ»
- дёҖеЈ°вҖңеҳҹеҳҹвҖқпјҢдёҖиӮЎеӯҗвҖң家еұһж„ҹвҖқи—ҸйғҪи—ҸдёҚдҪҸпјҢжҳҺжҳҫе®ЈзӨәдё»жқғе’ҢеҗҚеҲҶ
- 马зӯұжў…иҝ‘з…§еӯ•иӮҡжҳҺжҳҫпјҢиҮӘжӣқд№°жҲҝз”ұиҖҒе…¬еҶіе®ҡпјҢиҪ»жқҫвҖңжӢҝжҚҸвҖқжұӘе°ҸиҸІ
- йҳҝжІҒжӯЈејҸеҗ‘йЈһе„ҝд№җеӣўеҸҠйҷҲе»әе®ҒйҒ“жӯүпјҢжҫ„жё…вҖңиў«иёўеҮәвҖқжҳҜдёӘиҜҜдјҡ
- дёҚзӮ’иҜқйўҳдёҚдёҠз»јиүәпјҢдәҺе’Ңдјҹдёәе•ҘдёҠзғӯжҗңпјҹе®ҳеӘ’жҸӯејҖд»–зҡ„вҖңе°ҒзҘһеҜҶз ҒвҖқ
- жӣ№ж јеҘіе„ҝGraceиҝ‘з…§жӣқе…үпјҢд»ҺвҖңдё‘иҗҢвҖқеҲ°жғҠиүіпјҢеҰӮд»Ҡ16еІҒжјӮдә®еҲ°и®ӨдёҚеҮә
- йқ еёҲзҲ¶еҮәеҗҚпјҢиө°зәўеҗҺеҚҙвҖңеҸҚе’¬дёҖеҸЈвҖқпјҢиҝҷ4дҪҚжҳҺжҳҹзңҹжҳҜеҝҳжҒ©иҙҹд№үеҗ—пјҹ
- вҖңжңүд»Үеҝ…жҠҘвҖқпјҒз”©жҺүйҷҲдјҹйңҶпјҢзүөжүӢзҷҫдәҝеӨӘеӯҗпјҢиғҢжҷҜејәеӨ§еҲ°ж— дәәж•ўжғ№
- еҘ№жҳҜжқЁзҙ«й—әиңңпјҢеҮәйҒ“иў«иӘүдёәвҖңе°Ҹй«ҳеңҶеңҶвҖқпјҢеҰӮд»Ҡ31еІҒжҗӯжЎЈй»„иҪ©иў«еёҰзҒ«пјҒ
- еј йҰЁдәҲжҷ’иӢҸеҰІе·ұеҰҶе®№пјҢе–ҠвҖңи„ёеңЁжұҹеұұеңЁвҖқпјҢзҪ‘еҸӢпјҡиҝҷжүҚжҳҜзҘёеӣҪеҰ–еҰғ
- еҝ«д№җ家ж—Ҹдә”дәәе…Ёйҳөе®№еӣһеҪ’пјҒзҪ‘дј еӣўз»јгҖҠеҝ«д№җ家ж—Ҹзҡ„ж—…иЎҢгҖӢеј•зҲҶвҖңзҲ·йқ’еӣһвҖқзғӯжҪ®